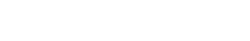并蒂双生花:再谈虚假广告与虚假宣传的界分
发布时间:2024-12-30
文 | 沈澄 汇业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一)广告和宣传的量子纠缠
谈广告和宣传的关系,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进行要件对比,通常的办法,是先识别什么是广告,剩下的就是宣传了。
例如,根据《广告法》第二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商品经营者或者服务提供者通过一定媒介和形式直接或者间接地介绍自己所推销的商品或者服务的商业广告活动。”可见,商业广告一般有4个构成要件:(1)主体要件:商品经营者或服务提供者;(2)主观要件:介绍自己推销商品或者服务;(3)形式要件:通过一定媒介和形式。(4)行为要件:直接或间接地推销。
在互联网背景下,广告的内涵和边界也许会伴随着媒介和形式的拓展而适当延展,然而涉及商业广告的界定时,仍应牢牢把握前述4个构成要件的判定。
以电商直播为例,根据主体要件,若主播并未受托于特定广告主,直播内容不在于向观众推销商品,直播目的也不是促进特定商家产品或服务交易,而是以“好物分享”“好物推荐”等形式分享自身产品或服务使用心得,进而吸引粉丝关注,增加账号流量,那么此时由于并不存在特定“广告主”及直播活动所指向的广告服务委托主体,因此不被认定为商业广告。再如,有一些直播活动并不直接带货,而是以营销品牌的方式进行品牌广告,从行为要件观之,属于“间接地推销”,仍不妨碍商业广告性质的构成。
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但是在实践中,仍然存在识别不清,或者一案双罚的情况。尤其是在执法层面来说,广告和宣传常常是不加区分的,而且这种区分障碍似乎存在着某种历史性的路径和执拗。例如,1993年版的《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不得利用广告或者其他方法,对商品的质量…等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该版非常明确的将虚假广告纳入虚假宣传的范围之内。而2017年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删除了“利用广告或者其他方法”,将虚假广告排除虚假宣传之内。2019年再次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仍保留了这一表述。具体如下:

从沿革来看,其实现行法律框架也试图将虚假的“广告”从虚假的“宣传”行列中剔除出去,但是实践中这种区分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本质上,还是由宣传与广告的上下阶关系所决定的,法律明确界分宣传与广告的分界难度较大。
(二)区分广告与宣传的价值
那么,为什么要区分广告和宣传?
这种区分对于具体案件中避免“一事双罚”“双重危险”而言,具有积极的意义。例如,有市监局执法人员即提出“如果企业简介中的内容有的构成虚假广告,有的构成虚假宣传,但基本都在同一个版面上,虽然同时违反了两部法律,但从行为来看是同一个行为,我们不宜将其硬生生拆开来视为两个违法行为,而应视其为同一个违法行为,适用《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的一事不再罚原则。”
不妨模拟几种情形:

以上示例大致可以看出,虚假宣传(《反不正当竞争法》)和虚假广告(《广告法》)的区分为实践中企业应对执法查处提供了转圜的余地和空间,从我们经手的相关案件经验来看,通过这种区分协助品牌方企业应对特定的广告违法事件,从而争取在个案中准确理解和适用法律规则协助企业豁免或减轻处罚、最大程度避免企业不必要的法律风险,保证行政执法部门准确把握执法尺度、合理运用裁量权具有重要意义。当然,对于宣传与广告的区分,我们仍然存在一些其他的担忧,并认为目前的立法行动可能为时尚早,具体请感兴趣的读者移步:“《不应将“虚假广告”踢出“虚假宣传”队列——对<反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第9条第2款的不同意见及反对理由》”。
(三)结语
实践中,有太多的人在没有搞清楚广告与宣传区分的情况下就开始贸然着手处理具体的广告违法或者宣传违法案件,可能在逻辑起点上就一叶障目的错误。这是一组因为长相酷似而容易推此即彼的脸谱化矛盾。
在这里,作者认为应当提请电商、品牌方和相关机构注意的一个重要误区,即:在“虚假或引人误解”问题上,虚假广告和虚假宣传的区分适用能够最大程度避免不必要的法律风险和提供案件处理的起点抓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