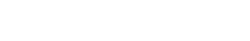制裁与仲裁系列问题:涉制裁纠纷的可仲裁性分析
发布时间:2025-05-19
文 | 傅靖宇 沈澄 汇业律师事务所经济制裁,被视为有效实现特定国家或地区政策目标的一种手段,目前存在普遍适用的趋势,尤其是俄乌战争以来美欧对俄罗斯的制裁几乎囊括所有领域。根据实施制裁的主体,经济制裁可分为
单边制裁和多边制裁:
单边制裁,通常是一国为维护其国家安全或实现其外交政策而实施的制裁。美国政府近来广泛实施的各类经济制裁就是典型的单边制裁。
多边制裁,系多个国家共同实施的制裁,不以实现某一特定国家的外交政策为目标。例如联合国制裁。
根据经济制裁指向的对象,又可以分为一级制裁(Primary Sanction)和次级制裁(Secondary Sanction):
一级制裁,旨在直接限制本国实体与目标国家/实体/个人的经济往来,约束对象仅包括制裁发起国的公民与企业等主体。例如禁止本国实体与受制裁国之间的的交易活动。
次级制裁,旨在限制第三国实体或个人与目标方进行金融和贸易往来,威胁对违反规定的第三国实体或个人实施惩罚,广泛限制任何第三方国家与制裁目标方的经济联系。例如,2024年美国《出口管理条例》修订,针对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OFAC)维护的特别指定国民清单(“SDN名单”)施加二级制裁,即如第三方主体为SDN名单中的实体提供实质性协助,无论该主体或交易有无美国连接点,美国财政部OFAC均有对其实施封锁制裁(blocking sanctions)的权力。
经济制裁通过干预私人法律关系达到制裁目的,扰动国际供应链,对合同的磋商签订、合同的性质、后续履行、争议解决等环节产生莫大影响,直接或间接地使履约变得困难、无利可图或不可能,大量国际商事争议由此产生。
因此,本系列文章将以经济制裁为出发点,分析经济制裁对国际商事仲裁的影响,涵盖商事仲裁的全流程,重点探讨国际商事仲裁受理阶段的经济制裁的可仲裁性,实体审理阶段经济制裁的定性的以及涉及经济制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
“可仲裁性”,是指某项争议或纠纷能否通过仲裁予以处理。涉及制裁的纠纷是否具有可仲裁性,一直存在争议。这一争议随着近几年国际政治环境和商业环境的变化显得越发重要。尤其是美国特朗普政府动辄进行的各类经济制裁已经对跨国投资和贸易造成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和伤害。为了解决因为制裁所引起的各类国际商事仲裁的实务难题,我们本文将首先聚焦于涉制裁纠纷的“可仲裁性”问题。
一、商事纠纷可仲裁性的判断
国际商事中以仲裁来解决纠纷的案件正在迅速增加,仲裁已成为解决跨国商事纠纷的主流机制。诉讼与仲裁作为两大争议解决方式,可仲裁性问题本质上是对商事仲裁活动受案范围的公共政策限制,其区分了哪些争议可以通过仲裁解决,而哪些争议基于其公共属性只能由法院管辖,可仲裁性涉及的是管辖权在法院和仲裁庭之间的分配,界定了契约自由之终点和司法公权之起点,代表着司法主权以及国家主权。
将争议提交仲裁解决需要以合法有效的仲裁协议为前提,依据仲裁条款独立性原则,基础商事合同无效不影响其合同中的仲裁条款的有效性,仲裁条款的有效性应当独立判断。裁庭判断仲裁协议是否存在、有效,以及解决仲裁协议应如何解释等问题,一般必须以某一国家的法律体系为标准和依据,即国际仲裁协议的准据法。在准据法未明确约定或约定不明的情况下,准据法的确定一般基于如下原则:对当事人是否有签订此类协议的法律能力产生争议,原则上应适用该方当事人的属人法解决争议;如果争议涉及仲裁协议本身的效力或范围,则应适用当事人选定的法律;在当事人没有确定准据法时,一般应根据仲裁地法确定。如《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纽约公约》”)第5条第1款规定,在当事人没有约定仲裁协议适用的法律,仲裁协议根据仲裁地法无效的情况下,法院方可以拒绝承认仲裁裁决,间接说明了仲裁协议有效性的判断准据法。同时,亦有国家根据国际私法中国际合同适用法律的一般原则,主张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国家的法律作为仲裁协议效力的准据法,尤其是在该争议涉及国家主权等层面时,赋予仲裁庭更多的自由裁量的空间。
一般仲裁条款的有效性要求包含两个方面:仲裁的意思表示以及仲裁事项具备可仲裁性。仲裁事项可仲裁性的判断标准各异,大致有如下评价标准:
1. 争议具备可处分性[1]。仲裁合意的意思自治存在的基础是私权的可处分性,因此只有当事人可以自由处分的事项才有权选择解决争议的方式。如荷兰《仲裁法》第1条明确规定“Any dispute relating to disposable rights, that has not been exclusively submitted by a special act to a court or to compulsory arbitration, may be submitted by the parties for decision by arbitrators.”
2. 争议的商事性。绝大多数国家对“商事”一词都尽可能作出广义的解释,一般包括所有类型的贸易或商业交易[2]。如《欧洲国际商事仲裁公约》第1条将该公约的适用范围限定于“自然人或法人为解决其相互间在国际贸易中发生的争议而缔结的仲裁协议”。
3. 争议的财产或经济属性。如我国《仲裁法》第2条对于仲裁事项的要求为“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并明确排除婚姻继承等人身关系诉讼以及行政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我国加入的(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的通知》第2条规将“契约性和非契约性的商事法律关系”定义为由于合同、侵权或者根据有关法律规定而产生的经济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主要落脚点依旧在于经济属性。经济属性的判断标准也极大地拓展了仲裁的适用范围。
4. 公共政策。实质上,可仲裁性隐藏的核心在于判断其是否符合社会公共利益,或者称为符合一国公共政策利益的保护。由于仲裁的保密特性,对于涉及公共利益纠纷,若整个仲裁程序甚至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无法公开被社会公众知晓,国家及其监管部门就难以有效监督。为避免国际商事交易当事人为了实现私人利益最大化,恶意利用仲裁来规避对其不利的强制性公法规范的适用,对于涉及公法或强制性规范的争议原则上将排除在可仲裁性事项外。
二、经济制裁对争议可仲裁性的影响
国际商事仲裁一般认为涉及公法制度而非完全由民商事法律关系引起的纠纷并不具有可仲裁性,经济制裁作为典型的公法规则,仲裁机构如何判定涉制裁纠纷的可仲裁性尚存争议。同时,可仲裁性问题还可能受到法院专属管辖规定的影响。
(一)仲裁合意有效
单边经济制裁是否具有可仲裁性的核心在于其是否符合社会公共利益,或者称为符合一国公共政策利益的保护。从国际商事仲裁实践看,支持涉及制裁纠纷具有可仲裁性的立场构成主流观点。
以Cantieri[3]案为代表,原告以针对伊拉克的经济制裁导致合同相关纠纷丧失可仲裁性为由向法院起诉要求损害赔偿,对此法院指出,只有当争议“涉及当事人无法自由处置的权利”时,方可根据意大利《民事诉讼法》第806条排除仲裁,而联合国与欧盟采取的国际经济制裁以及意大利为实施上述制裁制定的国内法,尚不足以致使当事人丧失自由处置合同的权利。因此,巴黎上诉法院终局性地认为该争议应当提交仲裁。
同样地,在Fincantieri[4]仲裁案中,仲裁庭认为涉及制裁争议的性质可能导致仲裁员适用公共政策规则,但并不意味着该争议因此变得不可仲裁。这一观点得到瑞士法院的支持,且瑞士法院进一步指出,根据瑞士1987年《关于国际私法的联邦法》第177条“任何具有财产性质的争议均可仲裁”这一宽泛标准,涉制裁的争议仍属可仲裁的事项范围。
(二)仲裁合意无效或被排除
有观点从仲裁员的私主体属性和仲裁的自治属性出发,认为仲裁程序无法裁断公法事务,因此,涉及经济制裁等公共政策范畴的商事争议并不当然具有可仲裁性。相反,该等争议应当交由国内或国际法院解决。反对者认为,该观点违背了作为商事仲裁基础的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即使仲裁庭在此过程中对公法规则的解释与法院的解释有所不同,也可容忍范畴,不能据此对当事人之间的仲裁合意断然作出否定评价。
但在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环境下,已经开始有国家或地区将涉经济制裁的实体纠纷列为法院专属管辖的范围,以法院专属管辖排除仲裁合意,否定了涉制裁纠纷的可仲裁性。以俄罗斯为代表,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作为被制裁国在涉制裁纠纷的可仲裁性问题上表明了与既有的欧洲实践相悖的截然不同的立场。针对西方国家对俄罗斯不断加剧的制裁,俄罗斯发展常态化反制裁模式,俄罗斯总统普京于2020年签署《关于修订俄罗斯联邦仲裁程序法以保护个人和法律实体在外国、国家联合和(或)联盟以及外国或国家联合和(或)联盟的国家(国家间)组织实施的限制性措施中的权利的法律》(“《制裁保护法》”),并在《俄罗斯联邦仲裁程序法典》增加第248.1条(俄罗斯联邦仲裁法院在涉及受限制性措施的人的纠纷中的专属管辖权)和第248.2条(禁令制度:对涉及受限制性措施的人的纠纷禁止在俄罗斯联邦境外的外国法院、国际商事仲裁提起或继续此类诉讼)。《制裁保护法》规定了对涉及受制裁的俄罗斯实体争议的法院排他管辖权,其法理依据是经济制裁使得合同中的争议解决条款变得“不可执行”。《制裁保护法》通过规定涉及制裁争议的“反制裁”专属管辖权,将管辖权作为反制裁工具,为受到西方制裁的俄罗斯自然人和法人单方面改变管辖权约定提供了法律依据。
实践中,俄罗斯当事人往往首先向俄罗斯法院申请禁令,在获取阻断域外仲裁程序的禁令后,请求俄罗斯法院行使“反制裁”专属管辖权。《制裁保护法》生效以后,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在乌拉尔公司案中所作的第309-ES-21-6955号裁决中认为,制裁至少在名誉上影响了俄罗斯实体的权利,将俄罗斯实体置于与其他人不平等的地位,因此有理由怀疑案件能否在实施制裁的国家获得公平的审理。因此申请人无需证明实施的制裁妨碍了其在国外诉诸司法,仅仅是实施制裁的事实就足以得出“诉诸司法的机会受到了限制”的结论。俄罗斯仲裁协会对此推定持明确反对意见,曾在该案中向俄罗斯最高法院提交书状,称在其他司法管辖区提出禁令申请的一方对拒绝司法的行为负有举证责任。
而后,在莫斯科市仲裁法院审理的BM-Bank公司诉Rizzani de Eccher股份有限公司案中,[5]法院加强对双方举证责任的要求,被申请人举证证明BM-Bank公司参与国际仲裁并不存在阻碍,事实上制裁并没有对BM-Bank公司参与国际仲裁形成阻碍。BM-Bank公司积极参与仲裁程序,又提出反仲裁禁令申请,构成滥用程序,莫斯科市仲裁法院因此驳回申请人BM-Bank公司的禁令申请。
可以发现,现俄罗斯法院并未采取极端保护的推定思路,而以个案审查为目标尽量还原法律事实,尽管在此过程中增加了被申请人的举证责任。[6]
三、商事主体的应对建议
对于商事争议可仲裁性的判断因法律适用上的差异具有较大不确定性,其核心是准据法对于争议是否具备可处分性的立场差异。
因此,商事主体在国际经贸活动中应充分考虑相关国家、地区法律对于争议可仲裁性的影响。对此,我们建议:审慎选择争议准据法。在合同磋商和起草阶段,一方面,应当充分了解拟选定(或因选定仲裁机构、仲裁地所指向)的准据法当中有关前述“争议可处分性”的认定规则,识别可仲裁性的风险边界;另一方面,还应当关注所适用的准据法项下对可仲裁性问题的司法实践、立法趋势乃至政策变动。
脚注:
[1] 参见赵学清、王军杰:《国际商事仲裁可仲裁性问题的历史演进及发展趋势》,载《国际经济法学刊》,2008年第4期。
[2] 参见韩健:《现代国际商事仲裁法的理论和实践》,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4页。
[3] Cantieri Navali ltaliani v Minisry of Defence of lrag (1996)21 Y.B. Comm. Arb. 594.
[4] Fincantieri Cantieri Navali ltaliani SpA and OTO Melara Spa v ATF ICC Award 6719 (1991).
[5] 案号:A40-50169/2022。
[6] 参见苏超:《论专属管辖权的反制裁功能——基于俄罗斯“反制裁”专属管辖权的立法和司法实践研究》,载《甘肃政法大学学报》,2023年第5期。
*团队成员施莹颖对本文有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