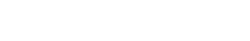仲裁协议范围在同一交易主体多合同关系中的延伸(上篇)
发布时间:2026-01-04
文 | 徐心悦 杨国胜 汇业律师事务所
本系列文章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主要聚焦于中国司法实践及其“狭义解释”立场,以及英美辖区的“宽解释”立场与仲裁范围推定原则。下篇通过借鉴若干英国典型判例,从多合同角度探讨仲裁协议在同一交易主体下如何延伸至相关协议及履约文件,以及延伸适用的边界,并就笔者近期参与的一起仲裁案件提炼出适用于国内仲裁协议范围问题的要素分析框架。
引言
在笔者近期参与的一起涉仲管辖异议纠纷案件中(下称“A公司诉B公司销售代理协议纠纷案”),当事人为合作之目的曾发生多份合同及相关交易文件往来,因部分文件未约定争议解决条款、部分文件含有仲裁条款,双方由此引发了关于仲裁条款效力的管辖异议纠纷。我方在一审中提出了管辖权异议并得到法院支持:一审法院裁定该案因当事人间存在有效的仲裁条款而不属人民法院管辖;对方上诉后,二审法院维持原裁定,案件最终转入仲裁程序。[1]该案在仲裁实务层面映射出一个重要问题:在司法审查程序中,若涉及当同一交易关系中存在多份合同文件、且部分文件含有有效仲裁条款(协议),法院如何认定涉案争议是否被当事人之间的仲裁协议有效覆盖。[2]换言之,在多合同关系下,仲裁条款的范围能否延伸至未明示约定仲裁的文件。
由于对该问题缺乏统一的裁判路径,本文以中国最高法院对仲裁协议范围采取的“狭义解释”立场为研究起点,结合英国Interserve v ZRE 案关于“争议是否落入既有仲裁合意的外延”的裁判思路,提出结构化的要素分析框架,以揭示仲裁条款在同一当事人多合同关系中的延伸适用与边界。[3]通过上述分析,笔者期望对律师在审慎设计仲裁条款时提供一些实务启发,也为司法审查仲裁协议范围补充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讨论维度,从而有助于稳定企业交易预期、提升商事纠纷解决效率。[4]
一、中国最高院的“狭义解释”立场与英美司法辖区的“宽义解释”理论
仲裁协议解释规则在仲裁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5]与其他合同条款不同的是,仲裁条款在合同文本中的表述较为公式化,以抽象概括的约定应对不可预见和瞬息万变的商业事件。[6]具体而言,大多数仲裁协议规定“因本合同引起的一切争议应最终通过仲裁解决”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应最终通过仲裁解决”。[7]由此引发出一个现实问题:将上述公式套用一切未来可能产生的难以预测的事件有时无法产生确定性的结果,尤其是在当今复杂的商业环境下,合同当事人往往在交易谈判的较晚阶段才纳入仲裁条款。例如引言中的A公司与B公司, 在磋商中期双方虽然正式在框架合作协议中合意采用了仲裁路径,从最终双方发生的纠纷来看,前述仲裁合意实际上无法预测到未来的影响。[8]正因合同条款中无法明确仲裁合意涵盖的争议事件范围,推定当事人的仲裁意图在法院处理管辖异议案件中或在司法审查程序中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最高院的狭义解释立场——以“江苏新誉”案为例
有学者认为,尽管中国法院整体上秉持支持仲裁的发展取向[9],但在仲裁协议范围的解释上,现行司法实践的立场与国际主流的广义解释原则仍存在一定偏离。[10]一方面,这一立场与我国仲裁制度的立法结构密切相关——在中国仲裁法的语境下,法院在涉及仲裁协议效力或范围的司法审查中,更容易基于《仲裁法》关于司法审查权限的相关规定,推导出法院对相关争议享有优先判断权的结论。例如,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2025)第三十一条延续了旧法在仲裁协议效力审查上的基本立场,即法院对涉及仲裁的管辖效力异议审查享有最终裁定权。[11]这意味着,法院不仅得以对交易中涉及的各项文件从实体问题层面进行审理,其对仲裁协议效力的确认也因此决定当事人是否得以将争议提交仲裁、仲裁机构是否获得管辖权,因而从制度层面强化了法院的狭义解释倾向。[12] 另一方面,几年前一起关于仲裁协议效力的纠纷中,中国最高院的指示同样反映了当前国内司法裁判对仲裁协议范围解释采取的谨慎立场。[13]
【裁判要旨】“……当事人双方于2007年2月4日就CRH-3和CRH-5项目签订的《技术转让协议》包含了将争议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的仲裁条款。2009年3月14日,双方又签订《谅解备忘录》,表示原则上愿意基于《技术转让协议》就CRH3-380项目的设计技术的授予和使用订立补充协议。之后,双方并未签订书面补充协议。
在本案审理期间,双方均认为确认本案仲裁协议效力的准据法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六条,仲裁协议应采取书面形式。仲裁作为一种双方自愿选择的争端解决方式,应当以双方明确的合意为基础。《谅解备忘录》表达了双方基于《技术转让协议》签订补充协议的意愿,但未明确表示《技术转让协议》的条款自动适用于CRH3-380项目,更未在《谅解备忘录》中订立仲裁条款,反而明确了双方在2009年4月30日前订立补充协议。从你院提供的案情来看,双方缺乏将涉及CRH3-380项目争议提交仲裁的明确的书面合意。故同意你院意见,应认定双方当事人未就CRH3-380项目争议达成仲裁协议,《技术转让协议》中的仲裁条款也不应适用于CRH3-380项目的争议。……”[14]
上述节选为中国最高院对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关于本案仲裁协议效力的指示。显然,最高院认为,即便新项目与先前的商业行为在主体、背景及合作内容上具有密切关联,仍不应仅以交易的连续性或项目的衔接性为由,推定先前合同仲裁条款的延伸适用。从上述最高院复函来看,其对涉案仲裁协议的解释有过于狭隘之疑:其一,上述认定实质上忽视了涉案争议与《技术转让协议》之间的关联性,反而强调新旧项目间的独立性,从交易行为的角度认定涉案项目不属于“原《技术转让协议》的项目范围”。[15]诚然,从实体问题的角度,涉案项目确实是当事人在先前交易的基础上达成的后续新合作,从合同文本的文义上理解,新项目及引发的争议均独立于先前的所有项目。然而,在双方为达成整体连续性商业交易目的合作背景下,当事人既然一致同意《谅解备忘录》为先前协议的补充协议,且并未在该补充协议中明确排除对原协议中仲裁条款的适用,从广义解释角度应合理推定双方在补充协议中延续原《技术转让协议》的仲裁合意。其二,从“但未明确表示《技术转让协议》的条款自动适用于CRH3-380项目”的表述来看,最高院显然关注的是在新的补充协议中,双方是否就沿用原仲裁协议存在明示的约定。换言之,最高院的立场可以解读为“除非当事人明确在后续补充协议中明示约定同意采用先前协议的仲裁条款,否则先前协议的仲裁条款不应适用于补充协议中发生的争议”反映了其在仲裁协议适用范围上所采取的狭义解释态度。[16]
(二)英美司法审查采用的仲裁协议范围推定原则
在当前英美国家司法管辖区中,对仲裁协议范围的解释通常采取广义解释的推定原则,即凡“与当事人关系有关”或“因合同引起或与之有关”的争议,原则上应假定(presumably)包含在仲裁条款内,除非当事人以清晰文义将其排除。[17]类似观点诸如,只要争议“可合理地解释为落入”一份广义仲裁条款的范围,就应当被纳入,除非当事人明确排除。[18]《纽约公约》亦对仲裁协议的解释采取亲仲裁的立场,其规定除非仲裁协议无效、失效或无法履行,法院应当尊重当事人之间的仲裁协议。[19]在实务层面,亲仲裁司法辖区中各国也存在不少适用推定原则的判例,例如,英国经典案例Fiona Trust v Privalov(2006)确立了著名的“理性商人推定”原则:理性商人通常意在将由其关系引起的一切争议交由同一仲裁/法院解决,解释仲裁条款应从这一一站式裁判(one-stop adjudication)的假设出发,除非条文清晰排除。[20]而纵观美国判例,Sourcing v Asimco一案中,第一巡回法院法官认为“在国际商业交易中,支持仲裁的政策更为有力”。[21] Moses H. Hospital v Mercury案中,美国最高法院采用“任何疑义应当以有利于仲裁的方式解决”的司法立场。[22]
上述推定原则的意义在于:其一,充分尊重当事人间的意思自治。[23]根据Fiona案的要旨,“将产生于同一合同的争议分配给不同的管辖裁判实在不利。因此,对于一个宽泛的仲裁条款,只有最具说服力的证据才能说服将某请求主张排除于仲裁以外之目的,尤其是当 被排除在外的事项含糊不清时”。[24]其二,这一推定原则可被视为英美司法辖区支持仲裁立场的直接体现。在司法审查程序中,为了确立仲裁协议范围,法院往往需要就当事人提交的大量证据进行实体审查,包括涉案主体资格、各项交易文件的关联等等。[25]这一过程通常很耗时,有时甚至长达一两年以上,不仅增加诉讼与仲裁程序的衔接成本,也破坏商事交易应有的确定性与时效性。对于注重交易效率与风险控制的商事主体而言,选择仲裁意味着当事人均不希望牵涉到冗长的司法程序中。因此,将公式化的仲裁条款(协议)解释为尽可能从广义角度纳入双方的争议,从这一角度反映了仲裁程序旨在促进国际经济与商业贸易的立场。
脚注
[1] 出于客户保密义务及正在进行的仲裁程序的保密要求,本文对案件相关的当事人名称、案号及其他足以识别具体案件的信息均作匿名化处理。所涉事实均已适度概括,不涉及任何可用于识别当事人的细节。
[2] 为行文便利,下文所称“仲裁条款”与“仲裁协议”具有相同含义,除非另有特别说明,不再加以区分。
[3] 参考脚注10.
[4] 出于比较性研究目的,为避免读者在比较法分析中产生混淆,本文在涉及各国判例时均明确标注其所属法域及法院层级,例如“中国最高人民法院”“英格兰及威尔士高等法院(EWHC)”“美国联邦第一巡回上诉法院”等。
[5] Gary B Bor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3rd ed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21) 1324–1326;Tibor Varady, John J Barceló III and Kevin M Clermont,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A Transnational Perspective (7th edn, West Academic Publishing 2019) 253.
[6] Born(注5)1324-1326页.
[7] 同上。
[8] 当事人在合同磋商阶段即全面预料到未来争议的范围在事实层面亦不可行。
[9] 姚宇:《对仲裁协议独立性的反思—以支持仲裁为视角》,载《河北法学》;姜丽丽:《紧跟时代步伐、创新探索仲裁司法审查裁判规则———最高人民法院第 36 批指导性案例评析》,载《人民法院报》2023年3月2日,第8版;宋连斌:《支持仲裁,依法监督,凝聚国际优选仲裁地的吸引力》,载微信公众号“人民法院报”2023年3月1日;刘敬东:《积极支持与监督仲裁的司法典范》,载微信公众号“人民法院报”2023年3月1日。
[10] Tietie Zhang, Narrow and Problematic Interpretation of an Arbitration Agreement’s Scope under Chinese Law (Kluwer Arbitration Blog, 22 January 2024). 本文所使用的“国际主流”一词,系沿引所引用文献作者的用语,仅为反映该作者对相关领域通行做法的概括性评价,而非本文作者基于独立的跨法域实证检验所作出的结论。鉴于本文篇幅及讨论重点主要聚焦于英美法系辖区(尤其是英国与美国)的判例,本文无意对包括德国、法国等大陆法系在内的主要法域进行全面梳理,亦不旨在为该用语建立穷尽性的比较法基础。因此,该表述系引用原文之措辞,而不应理解为本文已就所有主要法律体系之间存在该共识提供了充分论证。
[11]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2025)第31条。新《仲裁法》于2025.09.12 发布,并将于2026.03.01 实施。
[12] 崔宵焰:《国际商事仲裁协议效力之司法认定——兼评〈仲裁法(修订)(征求意见稿)〉第二十一条》。
[13] 为免歧义,在本章节下,所有关于“最高院”的表述均指代中国最高人民法院,不涉及其他任何司法辖区。
[1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申请人江苏新誉空调系统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KNORR-BREMSE ESPANA S.A.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纠纷一案的答复》([2016]最高法民他35号)。
[15] Tietie Zhang, Narrow and Problematic Interpretation of an Arbitration Agreement’s Scope under Chinese Law (Kluwer Arbitration Blog, 22 January 2024).
[16] 诚然,单一裁判材料本身并不足以穷尽整体司法趋势,然最高人民法院在我国裁判体系中的“方向标”作用,使其观点虽为一隅之见,却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可由此观察我国在仲裁协议效力解释上所呈现的狭义倾向。
[17] Born(注5, 1432页);; LawExplores, ‘Interpretation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Agreements’ <https://lawexplores.com/5-interpretation-of-international-arbitration-agreements/>; Vienna Law Review, ‘Interpretation of Arbitration Agreements and the Role of Applicable Law’ ; Tietie Zhang, Narrow and Problematic Interpretation of an Arbitration Agreement’s Scope under Chinese Law (Kluwer Arbitration Blog, 22 January 2024)
[18] Várady / Barceló / von Mehre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A Transnational Perspective,West Academic.
[19]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Arbitral Awards (New York, 1958), Articles II & V.
[20] Fiona Trust & Holding Corp v Privalov [2007] UKHL 40.
[21] Sourcing Unlimited Inc v Asimco International Inc, 526 F3d 38 (1st Cir 2008).
[22] Moses H. Cone Memorial Hospital v Mercury Construction Corp, 460 U.S. 1 (1983).
[23] 参见Tietie Zhang (脚注15)。
[24] Fiona (脚注24),参见Tietie Zhang(脚注15)。
[25]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