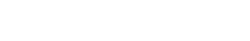境外公司法人人格否认中的法律适用博弈——基于《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14条“真实本座主义”适用的证成分析
发布时间:2026-01-26
文|朱䶮俊 汇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一、问题的提出:“刺破面纱”的规则落差与实务困境
1.实务背景:高频出现的“影子”香港公司与“隔岸观火”的内地股东
在涉外商事活动中,内地主体利用香港公司进行贸易、投融资已成为常态。这种公司架构在促进资本流动便利化的同时,也为债务逃避提供了天然的制度屏障。在大量涉外诉讼案件中,被告往往呈现出高度相似的特征:
主体特征:通常为一家在香港注册的私人有限公司,法定股本通常仅有1万港币,唯一的股东和董事均为持有内地身份证的自然人,或由另一家内地公司全资控股。
运营特征:该公司在香港没有独立的物理办公场所,仅挂靠在秘书公司的地址;没有香港本地雇员,甚至没有开设香港本地的强积金(MPF)账户;其银行账户可能开设在内地银行的离岸部(NRA/OSA),或者虽在香港银行开户,但网银操作IP长期显示为内地。
债务特征:以香港公司作为合同主体与内地债权人发生交易,一旦资金链断裂,债权人发现该香港公司名下空无一物,而其背后的内地股东却在内地拥有庞大的实业资产和高消费能力。
对于内地债权人而言,若不能突破公司独立人格的限制,其债权将沦为一纸空文。然而,要追究股东责任,首先面临的是法律适用问题。如果适用香港法律,债权人将面临极高的举证门槛;如果能争取适用中国内地法律,则可能利用中国《公司法》中相对有利于债权人的规则实现突围。
2.核心冲突:两地法律适用的巨大差异
法律适用之争,本质上是债权人保护门槛的高低之争。原告律师的核心策略是将管辖法律拉回内地,利用2023年修订的新《公司法》以及《九民纪要》中相对完善的股东责任制度;而被告律师的核心防线则是死守“登记地法”,利用其当地法律极高的证明标准构筑股东责任的防火墙。
(1)香港法(登记地法):坚守Salomon原则
香港公司法深受英国普通法影响,严格遵循Salomon v A Salomon&Co Ltd确立的法人独立原则。在香港法域下,“刺破公司面纱”(Piercing the Corporate Veil)被视为对公司法基石的挑战,仅在极少数例外情形下适用。根据香港法院在China Ocean Shipping Co v Mitrans Shipping Co Ltd 3 HKC 123案中的经典判词,法院只有在公司被用作“欺诈”(fraud)、“掩盖非法行为”(facade/sham)或“逃避现有法律义务”(evade existing legal obligation)的工具时,才会考虑揭开面纱。如果仅是为了规避商业上的债务风险而设立香港公司,则不在刺破面纱的范畴。
此外,在香港法下,即便是一人公司,其独立人格亦受到严格保护。原告必须承担全部举证责任,证明股东存在主观上的欺诈意图或滥用行为。单纯的“未足额出资”、“资产不足”或“一人控制”并不是刺破面纱的充分理由。对于内地债权人而言,要收集证据证明股东在设立公司之初就存有欺诈意图,在实务中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2)中国公司法(主营业地法):相对完善的债权人保护机制
相比之下,中国内地法律在处理“公司人格否认”问题上,展现出更强的实质正义导向和债权人保护色彩。《公司法》第23条不仅规定了纵向人格否认(股东对公司债务连带),还明确了横向人格否认(关联公司之间连带)。在《九民纪要》中,更是对人格混同、过度支配、资本显著不足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此外,《公司法》第23条第3款确立了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一人公司的股东如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此时如果法院决定适用中国《公司法》,原告只需证明被告是香港公司的唯一股东,举证的皮球就踢给了被告。
二、理论深层透视:第14条下的“主义之争”与规则异化
1.两大理论的博弈:内部事务主义vs真实本座主义
公司作为法律拟制的产物,其“属人法”的确定,本质上反映了一国法律体系对于资本自由与社会责任之间关系的根本看法。内部事务主义,主张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股东权利义务及责任等事项,应由公司注册登记地法律管辖。这是英美法系及当今国际商事惯例的主流。核心价值在于强调法律的“可预见性”和“确定性”。投资者在设立公司时即可预知适用的法律规则,降低交易成本。
而真实本座主义,则主张由公司的实际管理中心所在地法律管辖。其理论的核心逻辑在于,如果一家公司的决策中心、财务中心和主要业务地都在一国境内,即使该公司并非注册在该国,那当地法院依然拥有管辖权。其目的在于防止当事人通过在宽松监管地注册公司来规避本国强制性规范。
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14条的设计,体现了立法者在法律确定性与保护债权人利益之间的摇摆与折衷。这不仅是法条解释的问题,更是国际私法中“内部事务主义”与“真实本座主义”两大理论在中国司法体系中的投影与博弈。
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14条第1款的规定,法人的股东权利义务适用登记地法律,即该条款采用的是国际私法中的内部事务主义。但紧随其后的第2款则引入了这一制度设计的关键变量,“法人的主营业地与登记地不一致的,可以适用主营业地法律。法人的经常居所地,为其主营业地。”目前现有的法律及司法解释均未明确“法人经常居所地”的含义,这也导致了目前司法实践中对主营业地的认定标准也存在不一致。
同时,立法使用了“可以”而非“应当”,即法人的主营业地与登记地不一致时,既“可以”适用主营业地法律,也“可以”适用登记地法律。因这一“但书”条款实际上也赋予了法院在特定情形下适用真实本座主义的自由裁量权。
2.“例外”吞噬“原则”:真实本座主义在司法实践中的扩张
通过案例检索发现,在涉及债务逃废、股东滥用权利的案件中,法院倾向于通过第14条第2款进行“法律规避”的矫正。法院在认定“主营业地”时,往往采用实质重于形式的穿透式审查。在缺乏“经常居所地”明确定义的情况下,法院倾向于通过“实际控制人所在地”、“主要资产所在地”或“主要经营活动地”来推定主营业地。这种做法实质上导致了一个后果,即只要香港公司的股东常驻内地或主要业务往来在内地,内部事务主义(适用香港法)就有可能被真实本座主义(适用中国《公司法》)架空。
这虽然在个案中保护了内地债权人,但也引发了关于破坏法律适用确定性的争议。特别是对于那些确实开展跨国业务的香港公司,如果仅因股东在内地居住就被认定主营业地在内地,可能导致法律适用的混乱和对营商环境的冲击。
三、司法现状:对“经常居所地”的理解
1.“经常居所地”的判定逻辑与穿透式审判
通过检索案例,可以发现法院处理此类案件时,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定的裁判逻辑:以公司的物理存在否定其形式注册,以管理人员的行踪锁定实际本座。《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14条第2款规定“法人的经常居所地,为其主营业地”。司法实践中,法院认定这一要素的核心在于“人”(控制人)与“事”(业务)的结合。
在上海牵趣诉申通地铁广告合同纠纷一案【(2018)沪01民终5873号】,虽然牵趣公司注册在香港,但法院考察了其广告合同的履行地、广告投放地以及与内地关联公司的混同情况。如果一家香港公司的所有客户、供应商及收入来源均指向内地,即使其在香港有审计报告,法院很可能将公司的主营业地认定为内地。但笔者认为,法院在该案中的认定存在偏颇,如果仅仅以案涉的一份合同认定一个公司的整体业务经营情况,从而判断主营业地的方式是不妥的。
在(2024)津0319民初3218号一案中,董某为香港某公司的一人股东,同时该公司也仅有其一名董事。法院认为该香港重要管理决策和经营活动均在天津开展,在银行预留备注的对外联系地址亦在天津,据此可以认定天津即为香港某公司的主营业地。其逻辑链条为:公司是拟制人格->公司的意志由自然人(董事/股东)做出->董事/股东长期居住在内地且无出境记录->决策行为必然在内地发生->公司“大脑”在内地->主营业地在内地。
2.最高院对法人主营业地的辨证理解
在王加利、青岛光宇工艺品有限公司等不当得利纠纷一案【(2021)最高法民再138号】中,最高院认为:“诺华公司系为便于青岛光宇公司开展国外业务而由王某于香港设立,青岛光宇公司的应收货款通过诺华公司的账户汇入。争议货款亦系汇入了诺华公司的银行账户,既然诺华公司系为开展国外业务而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的香港公司,争议的款项使用了该公司的账户且已经进行相关操作,原审法院仅以未查询到王某在该公司存续期间有过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出入境记录为由,认定该公司的主营业地位于内地,事实依据并不充分,应在进一步查明相关事实的基础上,确定应适用的法律。”
在大林成名有限公司诉ATA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一案【(2022)最高法商初6号】,为证明被告公司的主营业地在中国,原告提交了一系列证据,包括被告公司在其官方网站发布的相关公告、公司年报、其向美国证监会提交的公开披露文件、电话会议纪要等,以此表明被告公司的主要办事机构、主要业务、客户、长期资产、高级管理人员及董事的办公地址、聘用的审计机构等均位于中国,故其主营业地位于中国。但最高院认为:“这些不能证明在北京相关经营场所的实体经营活动系被告公司直接负责,更不能证明被告公司开展实体经营的场所全部位于中国。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公司管理日益具有远程化、在线化的趋势,物理空间的办公场所在判断公司主营业地的标准问题上,权重日益受限。在缺乏进一步证据的情况下,不能仅因某实际经营场所出现过包含集团公司名称、商标或标识即将该经营场所所在某某集团公司的主营业地。”最终认定因被告公司在开曼群岛登记注册,故案涉董事会决议的效力应适用开曼群岛法律。
四、实务操作指引:锁定香港公司“主营业地”在内地的证据图谱
作为原告(债权人)律师为了说服法官适用第14条第2款,实现适用中国内地法律的目标,应搜集以下三类证据,构建“人、财、物”全方位的内地连接点证明香港公司仅具“躯壳”。以下为笔者基于代理的案件实务经验总结的证据图谱:
1.决策与指挥中心证据
ICRIS查册与NAR1文件分析:律师应登录香港公司注册处网上查册中心(ICRIS),调取该香港公司的最新《周年申报表》(Annual Return,Form NAR1)。
董事住址:香港公司法要求董事申报通常居住地址。如果董事在NAR1表格中申报的是中国内地的身份证号码和内地的居住地址,这直接构成了“公司决策者常驻内地”的强有力书面证据。但需要注意的是,根据最高院在(2022)最高法商初6号案的判例精神,物理空间的办公场所在判断公司主营业地的标准问题上的权重日益受限。
注册办事处地址:在实务中,绝大多数涉诉的“空壳”香港公司都挂靠在秘书公司地址(如香港九龙观塘、尖沙咀、湾仔等地的商务中心)。法院在认定主营业地时,会重点考察该地址是否具备物理上的经营条件。结合Google Maps,如果该地址同时注册了成百上千家公司,且无独立的门牌标识,法院倾向于认定该地址仅为“通讯地址”而非“主营业地”。
商业登记证(Business Registration,BR):查看“业务性质”(Nature of Business)一栏。如果填写为“CORP”、“TRADING”或空白,结合内地实际履约情况,可佐证其在香港无具体业务。如果填写了具体业务,需进一步核实该业务是否需要香港特定牌照(如金融牌照),若无牌照,则所谓的业务性质仅为虚构。
董事/实控人行踪:申请法院调取香港公司董事/法定代表人的出入境记录。如果记录显示该董事在相关年度内绝大部分时间在中国内地停留,且鲜有前往香港的记录,可证明公司的经营决策不可能在香港作出。
通信记录:双方往来的邮件、微信记录、钉钉审批记录。重点关注指令发出的IP地址、邮件落款地址、会议召开地点。如果董事会决议的签署地是在内地,或者股东会的召开地点在内地的酒店或股东家中,这是认定“经常居所地”在内地的直接证据。
印章的保管地址:申请法院要求被告披露香港公司的用印情况及印章保管地。虽然香港法下,签字的法律效力往往高于盖章,但很多商业合同签署时仍会加盖相应的签名章。如果能证明签名章保管于内地,则同样可以认定香港公司的管理中枢在内地。
2.资金与财务流转证据
银行账户信息:查明香港公司是否在内地银行开设了离岸账户(NRA账户)或自贸区账户(FTN)。NRA账户的开设本身就意味着其主要结算需求在内地,且受内地外汇监管。
审计报告(Audit Report)的利用:按照香港法的规定,香港公司必须进行年度审计。被告常提交香港审计报告以证明其合规性。原告律师应敏锐审查报告中的“收入来源地”、“纳税情况”、“薪酬”、“租金”等内容。
如果审计报告显示公司在香港利得税为零(申请了离岸豁免),或者注明“收入来源于香港以外地区”,这恰恰成为了原告的证据——证明其主营业地不在香港。此时,若被告无法证明在第三国(如韩国、新加坡)有实质经营,则按照“排除法”,内地作为实际控制人所在地和主要业务发生地,极易被认定为主营业地。
审计报告中有明确的租金和薪酬科目,这是判断香港公司是否实际经营还是躯壳的关键点。如果审计报告中的租金和薪酬科目金额较低,不符合常理,则可以判断出香港公司没有实际的员工和办公场所,极有可能是内地关联公司的员工负责日常业务。如果这两项科目有较为合理的金额,则可以要求被告提供金额相符的房屋租赁合同、员工花名册及薪资发放记录,以便核实香港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
针对审计报告中的营业收入科目,原告律师可以向法院请求香港公司披露其十大客户相对应的合同,如果合同的签订、履行均是在内地或者由内地的关联公司员工进行对接,则可以认定香港公司的主要营收来自于内地。
3.业务人员与物理存在证据
混同经营证据:调查香港公司是否与股东控制的内地公司共用办公场所、共用电话、邮箱后缀或前台人员。律师可前往内地关联公司的办公地点进行实地探访、拍照。如果在前台看到了香港公司的水牌,或者内地公司的员工名片上印有香港公司的职务,这是认定“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的关键事实。
员工社保与个税:调查香港公司是否有缴纳香港强积金(MPF)的记录。若无MPF记录,而其名义上的“员工”在内地缴纳社保或个税,则彻底击穿其在香港“实质经营”的抗辩。
4.举证责任的动态转移策略
在实务中,律师应巧妙利用举证责任的转移机制,制定庭审策略:
第一步(原告举证):原告通过查册NAR1文件证明被告注册地为秘书公司地址,通过出入境记录证明董事常驻内地,通过合同履行证明业务发生在内地。此时,原告已完成“主营业地在内地”的初步举证。
第二步(责任转移):此时,律师应向法庭主张:原告已尽到初步证明责任,举证责任应转移给被告。法院应要求被告提供其在香港有独立办公室租赁合同、当地员工社保缴纳记录、当地水电费单据等积极证据。
第三步(锁定胜局):若被告仅能提供注册证书和形式上的审计报告,而无法提供上述“生活痕迹”,法院极大概率会认定其未能推翻原告的主张,从而适用内地法律。这一策略在多起涉外商事案件中被证明行之有效。
五、香港法律查明的攻防战
如果法院最终认定应适用香港法律,原告律师并未完全战败。此时,战场将转移至域外法查明。香港法律查明在内地司法实践中相对成熟,但对于不熟悉普通法的内地律师而言,仍充满陷阱。香港法属于普通法系,其核心规则不仅在于成文法(如《公司条例》Cap 622),更在于判例法。
攻防点:被告方聘请的香港法律专家往往倾向于引用《公司条例》中关于法人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的条文,强调Salomon原则的不可动摇性。
原告策略:原告律师必须要求被告必须提供香港法院关于“刺破面纱”的完整判例体系,特别是最新的例外情形。
香港上诉法院在China Ocean Shipping Co v Mitrans Shipping Co Ltd一案中确立了重要的例外原则,这是原告律师在适用香港法时的主要突破口。
判例规则:该案确立,如果设立公司的目的是为了“逃避现有的法律义务”,法院可以刺破面纱。但仅仅为了“规避未来的潜在责任”,通常被视为合法的商业安排,只有针对“已存在”的义务进行逃避才是非法的。
因此,如果原告能证明,被告股东是在债务即将形成(如合同签约前夕)或已经形成时,通过设立或利用香港空壳公司来转移资产或承接债务,或者在诉讼期间突然变更董事、转移资产,这符合香港法下的“逃避现有义务”标准。如果能证明香港公司是在债务危机爆发后匆忙设立的躯壳,则有很大机会被认定为欺诈。
六、结语
随着中国司法机关涉外审判能力的提升,以及防止资本外逃和打击逃废债力度的加大,法院在处理涉及香港公司的案件时,法院更倾向于利用《法律适用法》第14条第2款的“主营业地”规则,贯彻“真实本座主义”精神,将那些实质上完全依附于内地的“假外资”拉回内地法律的管辖范围。但随着最高法在审判实践中的进一步细化,未来法院在认定主营业地时也将有更多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