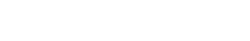Meta扼杀式并购缘何胜诉?法院为何多次提及TikTok?
发布时间:2026-02-06
编者按:近期Meta斥资20亿美元收购了人工智能初创企业Manus,引起我国监管机构的关注。而在此前Meta曾于2012年和2014年分别以10亿美元和190亿美元收购Instagram和WhatsApp,这两起并购被视为扼杀式并购的代表,美国执法机构FTC也于2020年就Meta的扼杀式并购行为向法院提起诉讼。然而,2025年11月美国华盛顿特区联邦地区法院判决FTC败诉。Meta的扼杀式并购缘何能够胜诉?法院又为何在判决书中多次提及TikTok?本文通过对Meta案判决的解读,探讨该案给平台企业并购监管所带来思考和启示。
一、案情概述
近几年来,美国司法部(DOJ)和联邦贸易委员会(FTC)针对大型平台企业接连发起诉讼,其中FTC于2020年针对Meta(原Facebook)发起的诉讼受到广泛关注。FTC指控Meta在2012年和2014年分别收购Instagram和WhatsApp的行为属于扼杀式并购(buy to kill or killer acquisition),而该等并购则属于违反谢尔曼法第二条的巩固垄断地位行为。 该案经过双方数轮程序动议之后,最终于2025年4月在华盛顿特区联邦地区法院进行了长达6周的庭审。2025年11月18日法院对本案做出一审判决。主审本案的博阿斯伯格法官(Boasberg)在判决书中指出,FTC主张的个人社交网络(Personal Social Network/PSN)相关市场定义过于狭窄,短视频社交媒体TikTok和YouTube都应被纳入同一相关市场,而FTC未能证明Facebook在这一更大的相关市场中占据支配地位,因此在无法证明Facebook具有垄断地位的情况下,自然也不存在巩固垄断地位的行为,据此判决FTC败诉,而Meta在本案中胜诉。 尽管FTC在本案中败诉,本案中美国执法机构和审理法院对于如何识别大型网络平台的潜在竞争问题所作出的一些探索性思路仍然值得关注,例如如何在巩固垄断地位行为案件中跳过先界定相关市场的间接证明方式,通过直接证据证明垄断地位;又例如对于大型免费网络平台如何认定其具有提高价格的能力,以及如何界定免费网络平台的相关市场,这些探索性的执法和审理思路尽管尚未有最终定论,其方法也值得我国实务界进行借鉴。本文将结合FTC诉Meta案,对上述执法和司法的创新之处予以介绍。 二、执法和司法创新 (一)证明垄断地位的直接证据 针对谢尔曼法第二条的垄断或意图垄断行为,传统的执法思路是首先界定相关市场,进而证明被告在相关市场具有支配地位,最后再证明被告的行为损害了相关市场竞争。这种传统套路经常遭到质疑,认为通过界定市场来判断被告的支配地位,是非常间接的替代性方法,既不准确,又给原告或执法机关带来巨大的负担。在本案中,FTC尝试跳过相关市场界定环节,通过证据来直接证明被告Meta具有垄断地位。 FTC直接证明被告Meta市场支配地位的证据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Meta长期获得远超资本投入的高额利润,其次是Meta有能力在不失去利润的情况下提高其质量调整价格(Quality-Adjusted Price),再次是Meta有能力利用质量调整价格对特定用户进行价格歧视。值得注意的是,博阿斯伯格法官并未否认FTC跳过界定相关市场、通过直接证据证明Meta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思路,而仅仅认为FTC所举出的直接证据,未能证明Meta具有支配地位。 举例而言,FTC主张Meta长期获得远超其资本投入的高额利润,在2024年的广告收入高达1610亿美元,这些足以显示其具有支配地位。然而博阿斯伯格法官认为,远超成本的高额利润固然可能是因为具有垄断地位,但也不排除是因为精明的管理、极高的效率、旺盛的需求或者高风险投资的回报。事实上,FTC未能排除掉这些同样可能导致超额利润回报的因素,相反Meta能证明其不断发展的精准定位消费者的广告推送技术,可以吸引广告主对其进行广告投放,而不是因为Meta能够牢牢控制消费者。据此,博阿斯伯格法官认定仅凭高额利润无法证明Meta具有垄断力,并且还引用了波斯纳法官的判词,指出从高额回报来推断支配地位是具有欺骗性的,就连经济学中都没有很好的理论可以证明这两者之间具有很强的相关性。与此同时,就FTC所提出的质量调整价格和价格歧视等直接证据,博阿斯伯格法官也逐一进行了分析,指出其未能证明Meta具有支配地位(关于有能力提高质量调整价格的主张,我们将在下文中展开介绍)。 作为对比,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在禁止滥用支配地位的行政执法案件中,普遍的做法是先行界定相关市场、论证支配地位,再分析限制性行为的竞争效果。例如,我国执法机构执法的阿里巴巴和美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中,均是遵循这一执法思路。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垄断民事诉讼领域,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在360诉腾讯案二审判决中,曾明确并非在任何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案件中均必须明确而清楚地界定相关市场。其认为“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的审理中,界定相关市场是评估经营者的市场力量及被诉垄断行为对竞争的影响的工具,其本身并非目的。即使不明确界定相关市场,也可以通过排除或者妨碍竞争的直接证据对被诉经营者的市场地位及被诉垄断行为可能的市场影响进行评估。因此,并非在每一个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案件中均必须明确而清楚地界定相关市场。”然而,除了上述案件之外,鲜有其他诉讼案件采用了通过直接证据证明支配地位的思路。 (二)免费平台如何认定收取垄断高价 在传统执法中,垄断者具有支配地位(垄断力)的主要表现,就是能够对消费者提高价格,同时不会因消费者减少购买而失去利润。然而,Meta案件中的一个难点就是Facebook和Instagram均是免费的社交平台,其对注册用户并不收费,更谈不上涨价。在此情况下,如何能够论证Meta具有提高价格的能力?前文提到,FTC在本案中提出了质量调整价格(Quality-Adjusted Price)这一概念,主张Meta有能力在不失去利润的情况下提高质量调整价格,以此作为直接证据证明Meta具有支配地位。这一执法思路也颇为新颖。 所谓质量调整价格,是假定每一名义价格,包括当社交网络平台对用户收费定价为零时,都会对应给予用户特定的内容和服务、以及用户需要被采集的特定信息和被占用的特定时间成本;倘若社交网络平台对用户的名义价格未调整,也即仍然为零,但是给予用户的内容和服务质量降低、同时用户的个人信息采集量增加、用户被占用的时间成本上升,这实际上相当于对应质量调整的价格上升。 FTC在Meta案中正是尝试使用质量调整价格,来解释即便Facebook平台对用户端的收费长期保持为零,也即免费,仍然可以通过降低内容和服务质量、增大用户信息采集和用户时间占用成本的方式提高价格。FTC着重从Facebook的广告投入量(ad load)持续增加、用户满意度(sentiment)下降以及减少对用户亲朋好友内容的推送(underinvestment in friends and family)等三个方面来进行论证质量调整价格在持续上升。 博阿斯伯格法官并未否认质量调整价格这一论证思路,但是认为广告投放量增加、用户满意度下降、亲朋好友熟人社区内容推送减少这三个方面,均不能推导出Facebook具有垄断地位。首先,关于广告投放量增加,博阿斯伯格法官注意到Facebook在增加广告投放的同时,也在不断增加Facebook的功能;另一方面,证据显示Facebook广告投放量增加的同时,广告自身的质量和与用户的相关性也在增加,因此并未降低用户的使用体验。综上,从广告投放量增加的角度,无法论证Facebook对用户的质量调整价格有所上升。 其次,关于用户满意度下降,证据显示用户满意度调查结果,往往是与用户对Facebook的情绪相关,而不是与Facebook自身的服务质量相关。举例而言,在剑桥分析公司揭露Facebook存在用户隐私和数据保护漏洞时,用户满意度曾大幅下降;而当Zuckerberg宣布将大部分财产捐赠给慈善事业时,用户满意度又大幅上升,而这些时候Facebook自身的服务质量事实均未发生明显变化。同时,即便在相同事情,用户使用相同版本的Facebook,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用户对Facebook的用户满意度也会不同。因此,用户满意度整体降低,更多的是与用户的情绪以及与行业的整体状况相关,并不能反映出Facebook具有支配地位。 再次,关于亲朋好友内容推送减少,博阿斯伯格法官指出,Facebook向用户推送内容的改变,并非是Facebook去压制用户并刻意推送用户不希望看到的内容,更真实的原因是用户自身的改变:一方面越来越少的用户愿意在公共平台发布个人信息,因此关注亲朋好友的动态能够给用户带来的信息越来越有限,另一方面,随着视频信息传输、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算法技术的发展,平台可以向用户精准推送用户个人更为关注的短视频内容和信息,因此现在的Facebook用户已经不再像早期那样主要去浏览好友上传的动态内容,事实上仅有17%的使用时间会阅读与亲朋好友相关推送内容,而大部分时间是浏览Facebook 通过Reel推送的视频内容,这些虽然是陌生人的信息,但却也是用户更乐意关注的内容。 (三)免费平台的相关市场界定方法 针对谢尔曼法第二条的垄断行为,如果无法通过直接证据证明垄断地位,需要回到传统的间接证明方法,也即先界定相关市场,进而判断是否具有支配地位,然后判断限制行为是否具有损害竞争后果。然而面对免费的社交网络平台,传统执法中的相关市场界定方法将受到挑战。例如,界定相关市场最常用的假定垄断者测试法(HMT),是通过价格的小幅度但有意义且非短时的持续上涨(SSNIP)来测试产品之间的替代关系,进而界定由具体产品组成的相关市场范围。然而,对于免费社交网络平台,这种测试方法难以实施,因为其并不向用户收费。 当然,执法机构仍然可以采用以质量调整价格来替换价格的方式,通过考察平台对用户服务内容和服务质量小幅度但有意义且非短时的持续下降(SSNDQ),来测试平台之间的替代关系,进而界定相关市场范围。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反垄断民事诉讼司法实践中,例如最高院审理的360诉腾讯二审案件,最高法院在判决书中也阐述了对于免费平台可以采用数量不大但有意义且并非短暂的质量下降(SSNDQ)”的方法作为相关市场界定的替代性方法。 然而, 在FTC诉Meta案中,法院更多地采纳了被告方提出的对平台之间替代性的直接观察(Observational Evidence)和实地试验(Natural and Field Experiments)的市场界定方法。 从直接观察证据来看,Facebook用户浏览网络平台应用的时间会直接在Facebook和TikTok以及Youtube之间选择和分配。Meta曾对5万名用户做过18个星期的跟踪调查,发现这些用户在不浏览Facebook或Instagram的内容时,首先会选择浏览Youtube的内容,其次会浏览TikTok的内容。另一方面,证据显示在2021年TikTok刚刚进入美国不久,Facebook的活跃用户使用Facebook应用的时间即下降了4-7%,而此时大部分活跃用户甚至还没有下载TikTok的应用,已下载TikTok应用的用户,使用Facebook应用的时间更是下降了17-26%。 从实地试验证据来看,判决书提到2021年10月Facebook曾经历数小时的服务中断,而此时选择其他应用进行替代的用户最多选择的是TikTok,其次选择的是Youtube。另外在判决书中还提到,2020年印度曾禁止用户使用TikTok,而在禁令实施2周之后,印度用户使用Facebook的时间相应增加了20%。同样,在2024年1月美国曾短暂禁止使用TikTok,而此时用户使用Facebook的时间也大量增加。 通过对以上直接观察证据和实地试验证据的考察,博阿斯伯格法官认为Facebook和TikTok、YouTube之间对于用户的时间分配而言具有直接替代关系。事实上这些不同平台应用在功能方面也越来越近似,Facebook用户最主要浏览的是通过Reel推送视频内容,而短视频网站TikTok和YouTube (Short)也在不断在推送内容中增加点评、互动、转发的社交功能。据此,博阿斯伯格法官认为,原来还可能存在的区分个人社交网络平台和短视频社交媒体的相关市场之墙,现在已经坍塌(While it Once might have made sense to partition apps into separate markets of social networking and social media, that wall has since broken down.) 三、结语及启示 尽管本案刚刚作出一审判决,FTC尚处于上诉期内,上诉二审结果是否会有变化尚不确定,但是判决所反映的针对大型网络平台潜在竞争问题的执法和审理思路,值得我国实务界予以关注。 首先,本案是围绕美国谢尔曼法第二条巩固垄断地位行为展开,而在我国针对涉嫌《反垄断法》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案件,也可以借鉴通过直接证据认定市场支配地位的思路。此外对于大型免费社交平台,如何通过质量调整价格认定其具有涨价能力,以及如何通过直接观察证据界定相关市场,均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其次,本案还涉及到美国法院对执法机构提出的所谓扼杀式并购理论的评判思路。可以看到,法院对该理论仍相对审慎,更关注并购的真实竞争效果。博阿斯伯格法官指出FTC主张的扼杀式并购缺乏竞争损害证据,事实上Instagram等应用在并购之后一直保持增长,不断推出新的功能,并未显示并购存在不利竞争效果。需要注意的是,我国《横向经营者集中审查指引》第62条也提及对初创企业进行扼杀式并购,并在第11条中提及“即有证据表明经营者实施集中的目的是排除限制竞争的,执法机构倾向认为该集中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考虑到FTC诉Meta案是扼杀式并购的重要参考案例,且该案起诉状中提及Meta创始人Zuckerberg曾多次在内部邮件中直言并购的目的是消除竞争,这些邮件也被作为该案重要证据,现在本案一审法院已判决FTC败诉,且博阿斯伯格法官强调并购后的实际竞争效果与FTC的假设不符,这一最新进展是否会影响我国执法机构对类似主观目的证据在执法实践中的运用,我们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 再次,本案还涉及对网络平台领域动态竞争的考察。博阿斯伯格法官在判决书开篇即引用了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名句——这个世界上唯一保持不变的就是变动本身、人不能踏进同一条河流两次(Believing that the only constant in the world was change, the Greek philosopher Heraclitus posited that no man can ever step into the same river twice),借此说明网络平台领域的动态竞争样态。在判决书的结尾处,博阿斯伯格法官再次回到赫拉克利特河流的比喻,指出甚至就连法院在历时五年的本案审理过程中,也未曾踏进相同的案情两次(the rapids of social media rush so fast that the court has never stepped into the same case twice)。在本案此前的程序动议审理中,双方甚至均未提及TikTok。而在最终的判决书中TikTok不仅被多次提及,还被视为与Facebook、YouTube相互替代、相互竞争的平台。本案也提醒我们,对于互联网平台领域的反垄断执法,应当更注重对动态竞争的考察,而不应仅限于对静态竞争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