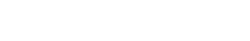中国法院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实践与应对
发布时间:2025-07-07
文 | 闵人瑞 汇业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前言
随着中国与全球经贸合作不断深化,跨境商事争议日益增多,国际仲裁因其中立性、保密性和可执行性,已成为解决跨境纠纷的主流方式。良好的营商环境离不开公正、便捷的争议解决机制,而外国仲裁裁决在中国的承认与执行,则是国际投资者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本文结合若干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对我国法院在审查外国仲裁裁决过程中相关问题的裁判思路和执行过程的核心争议进行梳理与评析。
一、前提:裁决籍属的确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23修正)》第三百零四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需要人民法院承认和执行的,当事人可以直接向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其财产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其财产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当事人可以向申请人住所地或者与裁决的纠纷有适当联系的地点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办理。”
该规定为外国仲裁裁决在中国法院得到承认和执行提供了基本法律依据,明确了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的前提须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换言之,三百零四条明确了判断是否属于外国仲裁裁决的标准是裁决籍属,而“仲裁地”(seat of arbitration)又对裁决籍属的确定具有重要意义。
201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八条对“仲裁地”予以规定,但并未对其概念进行明确[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八条: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仲裁协议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仲裁机构所在地法律或者仲裁地法律。],亦尚未突出“仲裁地”的法律意义,这是基于不具有涉外因素的境内争议中尚不需要发挥“仲裁地”的作用,长久以来我国司法实践中取而代之的是由仲裁机构所在地承载仲裁地的法律意义。
但值得注意的是,司法实践中却早已呈现出接纳通过“仲裁地”确认裁决籍属的判例。例如,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在(2014)三中民(商)特字第12398号一案中将国际商会在加拿大作出的仲裁裁决认定为是加拿大的仲裁裁决;在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7)浙04协外认1号一案中将国际商会在瑞士作出的仲裁裁决的国籍认定为瑞士。
2025年4月30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第八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书面约定仲裁地,除当事人对仲裁程序的适用法另有约定外,以仲裁地作为仲裁程序的适用法及司法管辖法院的确定依据。仲裁裁决视为在仲裁地作出。当事人对仲裁地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对,根据当事人约定的仲裁规则确定仲裁地;仲裁规则没有规定的,由仲裁庭根据案件情况,按照便利争议解决的原则确定仲裁地。”尽管草案尚未正式通过,但这一修订体现了我国仲裁立法进一步与国际仲裁惯例接轨的趋势。与此同时,随着对“仲裁地”概念的明晰,外国仲裁裁决的籍属确定问题进一步得到明确:
第一,由外国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作出的仲裁裁决,并非是在“另⼀缔约国领土内”作出的仲裁裁决,应视为中国的涉外仲裁裁决,属中国国内裁决,而非外国仲裁裁决[2]。
第二,对于常设于中国境内的仲裁机构,以及临时仲裁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作出的仲裁裁决,也应视为外国仲裁裁决,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互惠原则办理。[3]
二、审查: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司法审查标准
自《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the New York Convention on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Arbitral Awards)(“《纽约公约》”)1987年正式对中国生效以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等形式逐步构建起相对完善的承认与执行制度框架。
但实践中,仍存在境外仲裁裁决不被承认和执行的情况。根据《纽约公约》第五条[4]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我国加入的<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的通知》的规定,中国法院不予承认和执行域外国仲裁裁决主要包括如下七种情况:(1)仲裁协议无效;(2)仲裁程序中未进行适当通知或因其他原因导致一方当事人未能申辩;(3)构成超裁;(4)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程序违反约定的仲裁规则,或违反仲裁地法律;(5)仲裁裁决对各方当事人不具有约束力或者该裁决被撤销或停止执行的;(6)依据中国法律,争议事项是不能仲裁的;(7)承认或执行裁决有违中国公共政策。上述规定中,前五项由当事人主张后法院方可审查,而后两项则由法院主动审查。实践中,被申请人引用较多的抗辩事由为前三项:
(一)当事人之间不存在仲裁协议或仲裁协议无效
1. 不存在仲裁协议
中国法院对涉外仲裁裁决予以承认和执行的前提是存在合法、有效的仲裁协议。根据相关司法实践,仲裁条款的成立及有效须基于各方当事人书面协定。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康科迪亚贸易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英国油、油籽和油脂协会(FOSFA)第3948号仲裁裁决一案的请示的复函》中答复:“《纽约公约》第二条第一款规定仲裁条款必须以书面协定达成。第二条第二款规定书面协议是指当事人所签订或在互换函电中所载明的契约仲裁条款或仲裁协定。可见,《纽约公约》并不接受默示的仲裁协议。本案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双方之间有仲裁合意并以签署或者函件互换的方式达成了书面形式的仲裁条款,人民法院应不予承认和执行该仲裁裁决。”
2. 仲裁协议无效
在承认与执行涉外仲裁裁决的场合下,若当事人将无涉外因素的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裁决,存在被中国法院认定为仲裁协议无效的风险,相关仲裁裁决或不予承认。例如,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北京朝来新生体育休闲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大韩商事仲裁院作出的第12113‑0011号、第12112‑0012号仲裁裁决案件请示的复函》中,最高法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所望之信公司与朝来公司签署的《合同书》中的仲裁条款是否有效。根据你院请示所述的事实,订立《合同书》的双方当事人均为中国法人,《合同书》内容是双方就朝来公司在中国境内的高尔夫球场进行股份转让及合作,所涉标的物在中国境内,合同亦在中国境内订立和履行。因此,《合同书》没有涉外民事关系的构成要素,不属于涉外合同。该合同以及所包含的仲裁条款之适用法律,无论当事人是否做出明示约定,均应确定为中国法律。《合同书》没有涉外民事关系的构成要素,不属于涉外合同。该合同以及所包含的仲裁条款之适用法律,无论当事人是否做出明示约定,均应确定为中国法律。故本案当事人约定将争议提交大韩商事仲裁院仲裁的条款属无效协议”。
(二)仲裁程序中未进行适当通知
该条是实践中被引用最多的抗辩理由之一。为使各方当事人获得公平的机会陈述意见并被仲裁庭采纳,《纽约公约》并未列出详细的程序要求。我国法院在审查该条款时采取实质重于形式的方式,综合审查个案的通知方式、当事人参与程度及程序保障是否充分,以判断仲裁程序是否显失公平。
1. 轻微瑕疵并不必然导致通知程序不正当
例如在“斯芙拉公司与万晟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案”中,斯芙拉公司向仲裁庭提出仲裁申请,乌克兰工商会国际商事仲裁庭通过快递向万晟公司寄送仲裁材料,但邮寄凭证地址将BAIZIGANG ROAD误写为BAIRIGANG ROAD。邮单显示该邮件于2017年9月30日由“LISA”签收。万晟公司未参加仲裁庭审,乌克兰工商会国际商事仲裁庭作出仲裁裁决。随后,斯芙拉公司向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万晟公司则称,仲裁案件材料未有效送达,裁决不具有法律效力。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后认为,仲裁庭于2017年9月通过快递的方式向万晟公司寄送仲裁材料时,虽然寄送地址与合同载明的地址之间存在细微差异,但寄送地址的城市、大厦及公司名称均正确。经地图查询,万晟公司所对应的路,也仅为白子港路,不存在任何其他定位。根据以上信息,应认定快递的送达地址足以指向万晟公司地址,且快递的签收回单反馈也显示函件送达并被签收。根据乌克兰《国际商事仲裁法》第三条与乌克兰工商会《国际商事仲裁院仲裁规则》第十五条第5款规定,仲裁程序的通知可以通过邮寄送达。因此,涉案仲裁裁决不存在未适当通知万晟公司导致其未能参加仲裁程序的情形,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遂裁定承认和执行案涉仲裁裁决。
2. 若送达仲裁通知等文书至错误地址导致未能实际送达的将影响承认与执行
例如,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就黎某九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一案请示的复函》中,最高院查明并认定:“越南国际仲裁中心的邮寄方式为仲裁规则所许可,但寄送结果仍应实际达到或足以推定达到使接受邮寄一方获得‘适当通知’的标准。新中利公司的登记注册地址和争议合同中所载地址是同一的,即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北京路57号。越南国际仲裁中心仲裁庭有机会亦有可能按照正确地址送达。仲裁庭第一次以邮寄方式向新中利公司寄送有关仲裁程序启动的通知,但没有证据表明上述材料已经向正确的地址适当送达。第二、三、四次寄送地址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北京路50号’,均存在错误……鉴于2013年7月19日进行的第二、三次寄送内容为开庭通知、仲裁庭组成通知,2013年7月23日进行的第四次寄送内容为要求双方当事人提交案件材料,上述寄送内容均为当事人在仲裁程序中应当享有的重要程序权利并直接影响其申辩权的行使。结合本案仲裁被申请人在仲裁程序中没有应诉、没有选择仲裁员等实际情形,仲裁庭在送达方面未尽谨慎义务并已实际造成剥夺当事人申辩权的结果……综上,案涉仲裁裁决存在《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乙)项规定之情形,越南国际仲裁中心仲裁庭于2013年9月13日作出的仲裁裁决不应予以承认和执行。”
(三)因超裁导致不予承认与执行
我国司法实践的核心在于判断超裁部分是否具有“可分性”。《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丙)项明确规定,如果提交仲裁事项的决定可以与未提交仲裁事项的决定分开,则裁决中关于提交仲裁事项的决定部分应当得到承认和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美国GMI公司申请承认英国伦敦金属交易所仲裁裁决案的复函》中表示:“仲裁庭只能对GMI公司与芜湖冶炼厂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作出裁决,对GMI公司与芜湖冶炼⼚及芜湖恒鑫铜业集团有限公司三方之间的纠纷做出了裁决,超出了本案仲裁协议的范围。但本案中从最终裁决结果看,有明确裁决芜湖冶炼厂单独承担责任的部分,就该部分裁决而言,仲裁庭是有权裁决的。鉴于仲裁庭有权裁决部分和超裁部分是明确可以区分的,应裁定部分拒绝承认。”可见,最高人民法院在该案件中也强调了关于仲裁裁决执行项目可分性的规定,这体现了支持仲裁、避免因局部瑕疵全盘否定裁决效力的价值导向。
三、建议:优化外国仲裁裁决在我国承认与执行的对策
结合中国司法实践及《纽约公约》相关规定,缔约方应重点关注以下几点:
第一,应当选择《纽约公约》缔约国作为仲裁地,确保仲裁庭所做出的裁决可以在其他缔约国得到承认与执行。《纽约公约》是国际商事仲裁领域最为重要的公约,缔约国将适用该公约承认与执行在其他缔约国所作出的仲裁裁决,为仲裁裁决在不同法域的执行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第二,确保仲裁协议有效。基于上述分析,仲裁条款必须满足书面形式要求;此外,结合相关司法案例,我国法律未授权当事人将不具有涉外因素的争议交由境外仲裁机构或者在我国境外临时仲裁,因此无任何涉外因素的国内争议约定境外仲裁的情况存在被中国法院认定为无效的风险。
第三,兼顾裁决内容与执行的关系。仲裁机构作出仲裁裁决时通常不会统筹裁执之间的关系,从而导致部分仲裁裁决事项出现无法执行的现象。加之境内外法系、法规、政策之间存在差异,境外仲裁机构在作出仲裁裁决时一般也不会将中国法律及司法政策作为考量因素。由此,人民法院在受理申请承认和执行域外仲裁裁决案件时,不仅需要审查域外仲裁裁决是否具有不予执行情形,还应当审查其是否具有违反国内社会公共利益、相关政策等的情形。在不具有上述情形的前提下,则应最大程度尊重域外仲裁裁决的裁决内容。[5]
结语
我国司法体系设有涉外仲裁裁决的司法审查报告制度,旨在加强对各级法院拒绝承认和执行涉外仲裁裁决行为的严格监督,[6]这体现了我国营造仲裁友好型制度、强化司法支持,优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兼容并蓄的大国司法态度,积极完善仲裁法治体系,既彰显对国际规则的尊重,也为跨境经贸合作提供稳定预期。本文及后续的系列文章拟向从事跨境交易的中外投资者、企业主提供的明晰法律指引,旨在防范和化解对华投资过程中潜在的争议风险。
脚注: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八条: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仲裁协议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仲裁机构所在地法律或者仲裁地法律。
[2] 例如美国布兰特伍德工业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案、《全国法院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会议纪要》第⼀百条均明确境外仲裁机构以我国内地为仲裁地作出的仲裁裁决,应当视为我国内地的涉外仲裁裁决
[3]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2022修正)》第五百四十三条
[4] 参见《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1958年纽约公约)》第五条:
一、裁决唯有于受裁决援用之一造向声请承认及执行地之主管机关提具证据证明有下列情形之一时,始得依该造之请求,拒予承认及执行:
(甲)第二条所称协定之当事人依对其适用之法律有某种无行为能力情形者,或该项协定依当事人作为协定准据之法律系属无效,或未指明以何法律为准时,依裁决地所在国法律系属无效者;
(乙)受裁决援用之一造未接获关于指派仲裁员或仲裁程序之适当通知,或因他故,致未能申辩者;
(丙)裁决所处理之争议非为交付仲裁之标的或不在其条款之列,或裁决载有关于交付仲裁范围以外事项之决定者,但交付仲裁事项之决定可与未交付仲裁之事项划分时,裁决中关于交付仲裁事项之决定部分得予承认及执行;
(丁)仲裁机关之组成或仲裁程序与各造间之协议不符,或无协议而与仲裁地所在国法律不符者;
(戊)裁决对各造尚无拘束力,或业经裁决地所在国或裁决所依据法律之国家之主管机关撤销或停止执行者。
二、倘声请承认及执行地所在国之主管机关认定有下列情形之一,亦得拒不承认及执行仲裁裁决:
(甲)依该国法律,争议事项系不能以仲裁解决者;
(乙)承认或执行裁决有违该国公共政策者。
[5] 参见《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承认和执行域外仲裁裁决和法院判决十大执行案例》
[6]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仲裁司法审查案件报核问题的有关规定(2021修正)》第二条